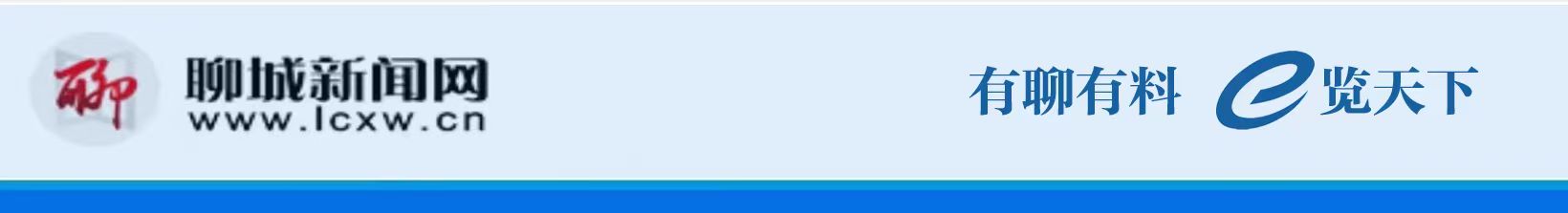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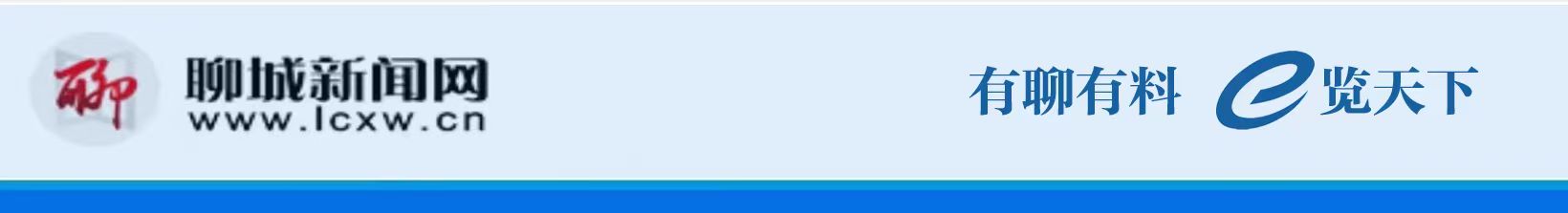
■ 朱明華
唐代詩人王維以“詩佛”聞名,其詩作以空靈禪意與山水意境見長。然而,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風順。開元九年(721年),王維因“伶人舞黃師子”事件被貶濟州(唐代的濟州在今聊城),開啟了一段深刻影響其創作與思想的貶謫生涯。本文從背景、詩歌主題及影響三方面,解析王維在濟州的詩歌足跡。
一、王維貶謫濟州的背景
(一)貶謫始末
王維(700年—761年),字摩詰,太原祁人,后隨父徙家于蒲州。張清華先生《王維傳·王維年譜》考證,其于開元九年(721年)春進士及第,釋褐為太樂丞;是年秋被貶為濟州司倉參軍,為主管倉庫的小官;在濟州謫居四年半,于開元十四年(726年)春寒食節前離開。
對于王維被貶謫的原因,《新唐書·王維傳》僅以“坐累”二字提及,至于因何“坐累”沒有明說。原文為:“王維,字摩詰,九歲知屬辭,與弟縉齊名,資孝友。開元初,擢進士,調太樂丞,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。”而《太平廣記》卷一百七十九給出了一個清晰答案:“(王維)及為太樂丞,為伶人舞黃師子(即黃獅子),坐出官。黃師子者,非一人不舞也。”“一人”,指皇帝,即這種舞只能為皇帝一人表演,“伶人舞黃師子”,是對皇權的挑戰,作為太樂丞的王維,自然對此事難辭其咎,因此“坐累”。有現代學者推測,王維被貶或與宮廷斗爭有關。因其早年與岐王交往甚密,可能卷入政治漩渦。
王維乃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當朝進士,從負責宮廷音樂事務的太樂丞,被貶至邊城濟州任司倉參軍,心理落差巨大。在即將離開京城到濟州赴任之時,王維寫下了那首著名的《初出濟州別城中故人》(一作“被出濟州”)一詩,抒發了對仕途的無奈與貶謫的悲涼,詩曰:“微官易得罪,謫去濟川陰。執政方持法,明君照此心。閭閻河潤上,井邑海云深。縱有歸來日,各愁年鬢侵。”詩中“濟川陰”,指位于古濟水之南岸的唐代濟州治所碻磝城(今東昌府區韓集鎮高垣墻村)。詩中,他感嘆自身官職卑微,極易獲罪,從而被貶謫至“濟川陰”;他感慨執政者執法嚴苛,而明君雖知曉自己的忠心,卻無力改變其被貶的命運;他描繪了濟州的偏遠與荒涼,并抒發了對未來歸期的憂思以及對自己前途命運的悲觀,感覺即使有歸期恐怕也要等到兩鬢斑白之時了。
(二)濟州地理與歷史沿革
唐代濟州治碻磝城,西臨黃河,其轄境包括今東昌府區、茌平區以及東阿、陽谷等縣。天寶十三年(754年),因黃河泛濫致使城毀,濟州遂并入鄆州。此地地勢低洼,水患頻發,環境頗為艱苦,與長安的繁華景象形成了強烈反差。
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》記載:“濟州,北魏泰常八年(423年)置,治碻磝城(今茌平區西南)。轄境約當今河南省范縣,山東省聊城、東阿、肥城、陽谷、高唐等地。隋開皇初廢。唐武德四年(621年)復置,轄境縮小。天寶十三載(754年),州城為河所陷,遂廢入鄆州。”此后的濟州一路南遷,歷經鄆城、巨野、任城等地,并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濟寧市(詳見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》“濟寧市”詞目)。
二、王維在濟州的詩歌創作主題
開元九年(721年),初入仕途的王維,本應意氣風發,卻意外從皇宮中的太樂丞被貶至黃河岸邊偏遠潮濕的濟州小城,擔任司倉參軍。身處異鄉的王維,孤獨寂寞,心情苦悶,只能通過尋僧問道,以獲取精神慰藉,緩解思鄉之情,撫平心靈創傷。在此后的四年半時間里,他在詩歌創作中一直呈現出這種心境,從而形成了以禪道哲思、隱逸向往、思鄉念舊等為主題的獨特風格。
(一)佛道交往與精神寄托
貶謫期間,王維與僧道往來較為密切,其詩作中已禪意初顯。如《魚山神女祠歌(二首)》,以描繪當地民間祈神求雨的場景作為載體,借助情景交融的筆法,把民間信仰的焦慮升華成對生命無常的禪意思考。魚山:又名吾山,位于今東阿縣南;當時東阿隸屬于濟州。
《魚山神女祠歌》其一《迎神》:“坎坎擊鼓,魚山之下。吹洞簫,望極浦;女巫進,紛屢舞;陳瑤席,湛清酤。風凄凄兮夜雨,不知神之來兮不來,使我心兮苦復苦。”《迎神》雖以民間祭祀場景為載體,卻暗含禪宗思想的深層映照。詩中“坎坎擊鼓”“吹洞簫”這般喧鬧的儀式以及“不知神之來兮不來”的表述,隱喻著真理不可從外在的聲色中尋求,而應當回歸于內心。
《魚山神女祠歌》其二《送神》:“紛進舞兮堂前,目眷眷兮瓊筵。來不言兮意不傳,作暮雨兮愁空山。悲急管兮思繁弦,神之駕兮儼欲旋。倏云收兮雨歇,山青青兮水潺湲。”全詩以祭祀儀式的“有”開篇,以山水自然的“空”收尾,層層摒棄世俗的妄念,最終指向“應無所住,而生其心”這一禪宗的終極境界。
在濟州期間,王維還與東岳泰山的云游道士有過交往,寫下了《贈東岳焦煉師》《贈焦道士》兩首詩。“煉師”是對道士的敬稱,后世學者認為焦道士與焦煉師為一人。
他在《贈焦道士》詩中寫道:“海上游三島,淮南預八公。坐知千里外,跳向一壺中。縮地朝珠闕,行天使玉童。”詩中描繪了海上仙島上的人物和景象,充滿了想象,極具奇幻色彩。
王維在《贈東岳焦煉師》中,通過“五岳遍曾居”“竦身空里語”“搘頤問樵客”等意象,勾勒出一位超然于世外的隱逸高士形象,展現他對脫離世俗的向往之情。
王維與東阿覆釜村崇梵寺僧人交往頗多,并留有詩作。
《全唐詩》在其《寄崇梵僧》題下注道:“崇梵寺近東阿覆釜村。”此詩寫道:“崇梵僧,崇梵僧,秋歸覆釜春不還。落花啼鳥紛紛亂,澗戶山窗寂寂閑。峽里誰知有人事,郡中遙望空云山。”詩中說,崇梵寺的僧人于秋天返回覆釜村,然而來年春天還未再來。詩人身處碻磝城中,唯有遙望那片空茫的云山。詩中“郡中遙望空云山”的“空”字具有雙關之意,既描繪了云山的縹緲之態,也喻示了內心的孤寂之感。
他還創作了等候和招待覆釜僧人的《飯覆釜山僧》一詩,詩中寫道:“晚知清凈理,日與人群疏。將候遠山僧,先期掃弊廬。果從云峰里,顧我蓬蒿居。藉草飯松屑,焚香看道書。燃燈晝欲盡,鳴磬夜方初。一悟寂為樂,此日閑有余。思歸何必深,身世猶空虛。”詩人借助佛法觀照,化解思鄉的執著,試圖通過對佛理的領悟以及對人生的思考,來沖淡思鄉之情,力求達到內心的寧靜,實現“寂為樂”的解脫境界。
(二)羨慕隱居與超凡脫俗
在濟州期間,王維創作了與賢隱往來并贊美隱逸生活的詩作。
在《濟上四賢詠·崔錄事》一詩中寫道:“解印歸田里,賢哉此丈夫。少年曾任俠,晚節更為儒。遁跡東山下,因家滄海隅。已聞能狎鳥,余欲共乘桴。”通過對濟州隱居賢人崔錄事品德的歌頌以及其隱居生活的描寫,表達出自身對隱逸生活的向往。
王維曾前往濟州趙叟家做客,并寫下《濟州過趙叟家宴》一詩:“雖與人境接,閉門成隱居。道言莊叟事,儒行魯人余。深巷斜暉靜,閑門高柳疏。荷鋤修藥圃,散帙曝農書。上客搖芳翰,中廚饋野蔬。夫君第高飲,景晏出林閭。”他覺得趙叟并非普通農夫,倒像是一位失意的讀書人,同時也認為趙叟的生活情趣頗似歸隱后的陶潛,悠閑自在,愜意非常。王維受“坐累”貶謫的影響,內心開始追求和向往隱居生活。
(三)關注現實與政治批判
在被貶謫濟州之前,王維曾因好友科考落地寫出“圣代無隱者,英靈盡來歸”的詩句,這既是對圣朝的辯解,也是對現實的隱喻性贊美。被貶謫濟州后,王維雖萌生隱逸之意,卻并未完全脫離現實,并且對社會現象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與思考。這種矛盾復雜的心態,為他后期選擇“亦隱亦官”的生活方式埋下了伏筆。
他在《濟上四賢詠·成文學》中寫下“中年不得意,謝病客游梁”,對流落于濟州的賢能之士成文學表達了深切的同情。他的《濟上四賢詠·鄭霍二山人》對現實的認識則更為深刻,詩中寫道:“翩翩繁華子,多出金張門。幸有先人業,早蒙明主恩。童年且未學,肉食騖華軒。豈乏中林士,無人薦至尊。鄭公老泉石,霍子安丘樊。賣藥不二價,著書盈萬言。息陰無惡木,飲水必清源。吾賤不及議,斯人竟誰論。”詩中“金張門”一詞,源自西晉文學家左思(字太沖)所作《詠史八首·之二》中的“金張藉舊業,七葉珥漢貂”。唐代李善在《昭明文選》卷二十一《詩乙·詠史》中注釋道:“功臣之后,惟有金氏、張氏,親近寵貴,比于外戚。”其中,“金”指的是金日 ,漢武帝在遺詔中命他與霍光共同輔佐昭帝;而“張”則指張安世,他在漢宣帝時擔任大司馬車騎將軍。王維在此處借“金張門”來比喻當朝的權貴之家。詩中體現了他對鄭公、霍公這些誠信博學之士不能得到舉薦的遺憾和惋惜,以及對朝廷用人不公的批判和憂慮。
王維對后他而來、又先他而去,且深受百姓愛戴的濟州刺史裴耀卿極為推崇。裴耀卿在濟州實行德政,治理得法,百姓安居樂業,社會秩序井然有序。他離開濟州后,濟州百姓為其立了功德碑,王維為之撰寫碑文,稱贊他為官清正廉潔,帶領百姓治理黃河決口、消除蝗蟲災害。在碑文的頌詞中,王維歌頌道:“童子何知兮,公邁成人;大不必佳兮,公德日新。天生德于公兮,遺此下民……;惠恤鰥寡兮,威詟黠吏;公之德兮,會無與二。人思遺愛兮,淚淫淫;歲久不衰兮,至今。性與天道吾不得聞兮,志其小者近者兮,已是過人之德音。”(見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二十六《王維三·裴仆射濟州遺愛碑》)。王維盛贊裴耀卿的政績與品德,在他離任之時,百姓戀戀不舍,他的事跡和精神也一直為后人傳頌。
(四)故舊重逢與情感慰藉
在濟州期間,王維創作了四篇與祖三有關的詩,分別是《贈祖三詠》《喜祖三至留宿》《齊州送祖三》和《送別》(一作“齊州送祖三”)。其中,《贈祖三詠》題下注有“濟州官舍作”。祖三即祖詠,排行第三,早年與王維相識于洛陽,開元十二年進士及第,次年赴地方任職時途經濟州。這四首詩,展現出期盼之情、重逢之喜及離別之悲。
《贈祖三詠》是王維在濟州因思念故舊好友祖詠所寫,詩中有“仲秋雖未歸,暮秋以為期。良會詎幾日,終日長相思”之句,滿含著對祖詠來濟州相會的期盼之意。
當摯友祖詠順道來濟州時,王維驚喜過望。他在《喜祖三至留宿》詩中興奮地寫道:“門前洛陽客,下馬拂征衣。不枉故人駕,平生多掩扉。行人返深巷,積雪帶余暉。早歲同袍者,高車何處歸。”其激動的心情展露無遺。
當祖詠離開濟州東去齊州時,王維寫下了《齊州送祖三》:“相逢方一笑,相送還成泣。祖帳已傷離,荒城復愁入。天寒遠山凈,日暮長河急。解纜君已遙,望君猶佇立。”此外,王維還創作了一首《送別》詩:“送君南浦淚如絲,君向東州使我悲。為報故人憔悴盡,如今不似洛陽時。”這兩首詩將相逢時的歡樂與分別時的悲傷描繪得淋漓盡致。祖三乘船遠去,王維卻在黃河岸邊久久佇立凝望。其依依不舍之情令人動容落淚,同時也深刻地反映出王維在濟州的形單影只和濃郁深沉的思鄉情懷。
(五)自然風土與鄉愁交織
王維在濟州期間創作了不少描繪風土的詩篇,并借以抒發思鄉之情。
他曾從碻磝城去往清河,沿途所見寫成了《渡河到清河作》一詩,詩云:“泛舟大河里,積水窮天涯。天波忽開拆,郡邑千萬家。行復見城市,宛然有桑麻。回瞻舊鄉國,淼漫連云霞。”“清河”,即清河縣,當時屬于河北道貝州清河郡,位于今河北清河西;“開拆”,指開裂,開元十年黃河博州段決口;“郡邑”,指當時的聊城縣。詩中展現了下游黃河的深沉、壯觀以及氣勢磅礴,描寫了乘船時所見到的平原地區良田萬頃、遍地桑麻,還有城鄉相連的繁榮景象。他在詩的最后所寫“回瞻舊鄉國,淼漫連云霞”之句,既體現出距離家鄉的遙遠,又抒發了對故鄉的深深思念之情。
王維還曾登上碻磝城樓,西望故鄉,并寫下了《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》一詩,詩曰:“高樓望所思,目極情未畢。枕上見千里,窗中窺萬室。悠悠長路人,曖曖遠郊日。惆悵極浦外,迢遞孤煙出。能賦屬上才,思歸同下秩。故鄉不可見,云水空如一。”《王維傳》作者張清華先生考證道,“西樓”,應是州郡碻磝城的西城樓,詩題中提到的使君五郎應是濟州刺史裴耀卿。王維與他同登此樓,舉目有感,對方寫了一首“西樓望遠思歸”詩,之后王維和了這首詩,兩詩皆為登樓遙望故里之作,主題同為“思歸”。王維“思歸”詩,字里行間都充滿了對故鄉的深深眷戀以及急切歸鄉的渴望。
后世學者通常將王維的《寒食汜上作》(一作“途中口號”)一詩,視為其離開濟州的時間標志。此詩云:“廣武城邊逢暮春,汶陽歸客淚沾巾。落花寂寂啼山鳥,楊柳青青渡水人。”在寒食時節,氛圍蕭瑟冷清,王維孤獨寂寞地行進于西歸之路,不時用巾帕擦拭思鄉的淚水。“廣武”:古城名,原址在今河南滎陽東北的廣武山上;“汶陽歸客”:濟州位于汶水之北,王維從濟州渡汜水返歸京城,故自稱汶陽歸客。
王維的這些作品不僅是其貶謫生涯的情感寫照,更反映了他在孤獨中通過佛道思想與自然山水尋求慰藉的心路歷程。他的這段貶謫經歷,重塑了他的內心世界,奠定其佛教禪意詩風形成的思想基礎。
三、濟州經歷對王維的影響
貶謫至濟州,王維遭遇了人生的低谷,他曾自謂在濟州期間“平生多掩扉”,意即常常大門緊閉,與人交往甚少。這一時期,他的詩歌創作既反映了濟州的地域文化,也展現了他內心的苦悶與無奈;這一時期,他寄情佛道、羨慕隱居,并逐步演化形成其后期詩歌“詩中有禪”“空靈超逸”的藝術風格。
(一)生活方式的轉變
貶謫前,詩文、書畫皆精,音樂造詣亦高的王維,前途可謂一片光明。《太平廣記》及《唐才子傳》記載,王維“年未弱冠,文章得名,性嫻音律,妙能琵琶,游歷諸貴之間”。他借助岐王及九公主之力成為“解頭”,后世稱之為狀元,已然躋身于上流社會。
濟州貶謫對王維影響深遠,促使他追求隱居靜修、持齋禮佛的生活方式。此后雖回京歷任右拾遺、監察御史、給事中乃至中書舍人、尚書右丞等職,卻始終未能撫平精神創傷,終其一生在仕隱之間徘徊。
晚年的王維長居輞川別業,亦即藍田別墅、終南別業。他齋戒誦經,參禪悟道,居所近乎與世隔絕,唯以清心寡欲為志。《舊唐書·王維傳》記載:“維弟兄俱奉佛,居常蔬食,不茹葷血;晚年長齋,不衣文彩。”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后,他于輞川“輞水周于舍下”,與道友裴迪“浮舟往來,彈琴賦詩”,輯錄田園詩成《輞川集》。在朝時“日飯十數名僧,以玄談為樂”,退朝后則“焚香獨坐,以禪誦為事”,齋中僅置茶鐺、藥臼等物,簡樸至極。妻亡后獨居三十年,“屏絕塵累”,終以詩佛之境超脫世俗。
(二)詩風的升華與禪意化
受貶謫濟州經歷的影響,后期的王維愈發篤信佛教,其詩作中也常常蘊含著一定的佛教禪意,能讓讀者感受到一種超越塵世的空靈與解脫之感。例如《竹里館》中“獨坐幽篁里,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來相照”,詩人獨坐竹林,彈琴長嘯,與明月相伴,營造出一種清幽靜謐的氛圍,體現出其內心的寧靜與超脫。再如《鳥鳴澗》里“人閑桂花落,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,時鳴春澗中”,通過對桂花飄落、春山空寂、月出鳥鳴等景象的描寫,展現出一種空靈、靜謐的意境,傳達出詩人對自然和人生的深刻感悟。還有《終南別業》中“中歲頗好道,晚家南山陲。興來每獨往,勝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窮處,坐看云起時。偶然值林叟,談笑無還期”,描繪了詩人漫步山間、隨遇而安,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景象;表達了他享受隱逸生活的愜意以及對待人生無常的豁達態度。這與他在《初出濟州別城中故人》詩中流露出的對自身命運遭遇難以釋懷的心境,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王維的濟州生涯是其人生的重要轉折點。貶謫所帶來的苦悶催生了隱逸思想以及禪意詩風,讓其詩歌兼具藝術的高度與哲學的深度。濟州的風土人情、宗教氛圍以及人際交往,共同塑造了“詩佛”的精神世界,使他的作品在唐詩中別具一格,成為跨越千年的文化珍寶。
2025-04-21 11:02:36
2025-04-21 10:59:25
2025-04-21 10:58:56
2025-02-13 10:19:29
2025-01-03 09:12:18
2025-01-03 09:11:3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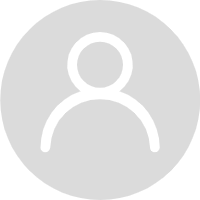
聊城新聞網 2006-2025 版權所有 聊城市新聞傳媒中心/聊城市政府新聞辦公室 聯合主辦
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:37120240004 魯ICP備09083931號 ![]() 魯公網安備 37150202000134號
魯公網安備 37150202000134號
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編號:115330086 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許可證(魯)字第720號
本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:18663509279 舉報郵箱:liufei@lcxw.cn
